“為什么李錄如此成功?我覺得部分原因在于,他可以說是中國的沃倫·巴菲特。”這是查理·芒格2019年在每日期刊公司年度股東大會上演講中的一句話。
查理·芒格視李錄為“房間里最聰明的人”,將其部分家族資產直接交由李錄打理。李錄先生也與芒格保持了亦師亦友的關系。
李錄先生的喜馬拉雅資本自1997年成立以來,成績顯赫。也應了芒格最喜歡的那句話——“我的劍傳給能揮舞它的人”。
今年11月28日,在查理·芒格去世一周年之際,我們與李錄先生進行了一場跨太平洋的訪談,李錄先生回憶起與芒格在一起的歲月,以及芒格作為現實中榜樣的言傳身教;我們聊到了芒格的價值投資與人生理念,也聊到很多內幕花絮,比如馬斯克與芒格見面時的思想碰撞……當然,還有更深層次對AI和人類文明的思考。
以下為訪談內容。
受訪:李錄 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
采訪:孫允廣正和島內容總監、微信主編
編輯:張啟玉
來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芒格去世這一年
孫允廣:在價值投資領域,您是資深前輩,并且跟查理·芒格先生交往頗深。今天(對談日期為2024年11月28日)非常特殊,是芒格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日,我想先請您談談這一年來的思考和感受。
李錄:如你所言,今天極為特殊,是查理逝世一周年,又逢美國感恩節,的確勾起我很多回憶。
我跟查理第一次長時間交流是在2003年的感恩節,聊了大概四五個小時,之后我們便成為了合伙人。時光飛逝,直到他去世,一晃就是二十年。
查理去世那天,晚餐時還一切安好、談笑風生,到吃甜點時卻感覺不適,隨后離開。次日清晨被送往醫院,約一天后與世長辭。他這一生都遵循固定的生活模式,有工作和家庭的陪伴直到最后一刻。
過去這一年里,我家中也遭遇悲劇,最大的女兒在查理去世數月后意外離世,兩三個月內,我失去了查理這位如父親般的人物以及我的女兒,真切體會了失去的痛苦。
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也讓我對人生有了更多感悟,其中一點便是,真正所愛之人其實從未離去。我能深切感受到,查理和我女兒茱莉亞仿佛時刻都在身邊,就像老話說的:精神是永恒的。
孫允廣:為您遭逢的變故感到難過,愿您節哀。您有一篇文章回憶了與芒格先生共進早餐、無話不談的經歷,這樣的經歷給您帶來了什么?
李錄:最開始我們是約在7點吃早餐,查理的太太去世后,我們改約了時間。
美國有一本書叫Tuesdays with Morrie《相約星期二》,講述一個年輕人和一個老者約在周二的晚餐故事,于是我們就也選在周二一起吃晚餐,其間無話不談。
我從小就讀了很多傳記,在古今中外找人生榜樣,因為我覺得人都是需要榜樣引領的。但現實中,以真人為榜樣很難,因為真人總有不足,就像我們說的蓋棺論定,一個人去世之后才能被完整評價,活著的時候我們要接納人的復雜性。
查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讓我有了一個人生中真實的榜樣。
不論早餐還是周二晚餐,我們隔幾天就要交流,對我來說,這二十幾年實打實的相處,他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很多行為還一直激勵著我,這樣的經歷獨一無二。
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有一種共識,查理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這一生都在探尋普適的智慧并且的確獲得了偉大的成就,就像一座豐碑。
他通過學習去獲取智慧,用智慧去行善、去獲得世俗的成功,然后用成功來幫助社會,用自己的榜樣給世界、給后人留下一份精神遺產。
再談價值投資
孫允廣:芒格和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在國內深受認同,您長時間與他們接觸,能否從您的視角,梳理一下芒格的投資哲學?芒格常說的“我的劍留給能夠揮舞它的人”,該如何理解?
李錄:關于價值投資,首先,查理接受本·格雷厄姆的原始闡述,也就是三條重要理念:其一,股票是公司所有權的一部分,并非只是一張紙;其二,市場存在是為了助力真正的價值投資者,而不是指引你怎么做;其三,投資要有足夠的安全邊際。
查理極為尊崇這三個基本原則,并且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了另外兩個獨到的貢獻,這和他所處時代的相關。
一方面,在他看來,有效投資的秘訣在于以合理的價格買入那些處于自己能力圈內、能夠真正理解的少數偉大公司,隨著公司價值本身的增長而增長,并長期持有。
另一方面,他獨特的貢獻是拓寬了價值投資的范圍。
他有個著名的說法,投資如同釣魚,有兩條重要規則,一是要去有魚的地方釣,二是不忘第一條。他認為投資要尋找容易建立能力圈且有更多選擇的地方。遵循這個理念,價值投資的范圍從專注美國被嚴重低估的公司,拓展到美國高速增長的偉大公司,再到美國之外處于增長期的偉大公司,讓價值投資在全球的實踐成為可能。
過去30年我所踐行的價值投資理念在全球的實踐和推廣,和查理的第二個理念契合,所以芒格家族部分財產由喜馬拉雅資本打理,二十幾年來我們結下多層面緣分,既是合伙人、朋友、師生,我和查理最小的兒子年齡相仿,某種意義上又如父子。
沃倫談及和查理的關系時也提到很多層面,在諸多意義上,將查理比作伯克希爾的設計師,而自己是工程總包,他是合伙人、摯友,因為查理比他大6歲,他們有時也有點像父子關系。
孫允廣:您剛提到了查理所說的“要去有魚的地方”,自20世紀中葉至今,世界經濟都處于高速發展期,而如今全球經濟“新常態”,黑天鵝不斷,“價值投資”的理念是否過時了?
李錄: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價值投資理念時,正值美國深陷長期大蕭條。1929年美國股市登頂后,一路低迷,直至1954年才重回高位。其間,世界大戰、經濟大危機接連爆發,美國失業率飆升至25%,全球都深陷戰火,遠比當下局勢嚴峻得多。
相較當時,如今的大環境已然不錯。價值投資正是萌芽于這種非常態時期,并非興起于高歌猛進的繁榮期。
正因如此,查理和沃倫談及成功時,總會強調運氣的關鍵作用,直言當初設想再多,也沒料到能收獲這樣的斐然成就。他們原以為所選投資方式穩扎穩打、不會失利,取得一定成果在意料之中,可如今這般舉世矚目的成功,屬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運氣、偶然因素是一部分,但價值投資確實為艱難時刻所準備。當然,形勢好的時候表現會更佳。所以,在當下,價值投資不但可行,更應該付諸實踐,畢竟相較之下,其他投資風格面臨的風險更多。這里說的風險,并非短期波動,而是長期資本的永久性損失。
孫允廣:我們常說“時間的玫瑰”“時間的朋友”,我有個問題,其一,我們做價值投資,是不是一定要堅持很長時間呢?也就是說時間是不是必備條件?其二,很多價值投資者都會遇到失敗,失敗與失敗之間的區別是什么?
李錄:你說得很對,價值投資在中國起碼算是被廣泛認可的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講,一方面是因為巴菲特、芒格極其成功,再加上他們理念的傳播,另一方面可能也得益于官方的提倡。
嘴上說的價值投資和實際踐行的價值投資差別很大,所以判斷是不是真正的價值投資得看最終結果。而看結果時,很多人習慣看買賣后的結果,這就又繞回到時間、業績、短期、長期、周期這些方面,所以有時候除了用這個詞,其他思維并沒有改變。
孫允廣:是存在一些知行不合一的情況嗎?
李錄:是這樣的,但也不一定就是知行不合一,可能是根本不知。
我做了30年實踐,遇到過全球各個地區很多投資人,我的感覺是,價值投資其實一直都是極少數人的選擇。
沃倫也講過,他說價值投資理念就跟打疫苗一樣,有些人有用,有些人則沒用,打完就知道了。能否接受,與一個人的品性密切相關,和短期業績沒什么關聯,和他做什么高度相關。
價值投資也不完全取決于時間,有些好公司,你可以長期和它共同成長。但有時候也會犯錯,犯錯了就得馬上糾正。有時候會發現更優秀的標的,那也會選擇賣出,價值投資不是買入后就不能賣了。有時候,作為資產管理人,如果投資人要贖回,那也沒辦法。
短期業績方面,在較短時間內,很多人業績也很好,甚至超過巴菲特、芒格,但長期能與他們比肩、超過他們的,到現在一個都沒有。當然,他們做了60年時間很長了。能長期堅持這種理念去做的人確實少之又少,這在某種意義上也說明這確實很難。
孫允廣:除了比亞迪,還有哪些例子,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芒格的投資理念呢?
李錄:比亞迪并非我們持倉最久的公司,我們持有了大概22年。在這期間,至少有六七次它的股價下跌超過50%,有一次甚至跌了80%。但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并沒有覺得壓力很大,因為我們一直清楚它每年都在創造新的價值。
所以理解公司所創造出的價值極其重要,當價格和價值出現偏離時,就可以有選擇性地增持,這些都是機會。
過去30年里,我們投資的項目挺多的,不管是在美國、亞洲其他地區,還是在中國都有投資。
不過對于查理來說,我覺得從他身上學到最多的一點,就是他一輩子都在持續學習,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比如,查理很少做投資,他時常會閱讀,像他閱讀《巴倫周刊》長達50年,其間只據此做了一個投資,但他每個禮拜都會去讀,對很多事物他都是如此。
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一次是,他99歲這年投資了一支人人都瞧不上的股票,我們都知道查理去世時距離100歲只差一個月,而在他去世的前一周,這支股票居然有了翻倍的收益。
我很欽佩他到99歲時,依然對投資持有熱情。他一輩子都在學習,一輩子都在堅守自己的原則。一直到去世前一天,他的生活基本沒什么變化,這就是他一直堅持的理性原則的一部分。
芒格的理性的四個層次
孫允廣:您剛提到了查理的“理性”,很多企業家做決策時未必完全理性,有時是憑借一腔熱情和企業家精神,如何理解其中的邊界?
李錄:查理講的“理性”和我們絕大多數人的理解不大一樣,它至少包含四個層次。
1.普世智慧
查理說的理性的第一個層次,是普世智慧。他花了一生時間去研究各種成功與失敗案例,這些普世智慧是從真實歷史中總結出來的,其中包含了企業家在關鍵時刻的決策等內容,它不只是數學邏輯,講的是真實世界里用成功和失敗兩種方式總結出的智慧。
2.柵欄式思維
第二個層次,他研究普世智慧要從人類所有學科里去總結、學習,也就是所謂的柵欄式思維。
他把人類研究各方面總結出的最重要成果都研究一遍,然后將它們融合在一起,去應用面對的問題。因為我們面對的問題本身就是現實中極為復雜、涉及各方面、關乎世界本源的問題。我們做研究時會把它拆分開來學習,但應用時需要綜合運用,所以必須把這些整合到一起,就像編織成網狀、柵欄式的。
世界的本源就是這樣,比如數學、物理、化學等,要想研究本質問題,不能只懂化學而不研究其他學科。人類已掌握的所有有意義的知識,都要相互關聯起來,使用時能協同運用,千萬不要有學科間狹隘的障礙,也別給自己設置這類障礙。
3.人類誤判心理學
第三點,是查理對整個世界的原創性貢獻,也就是人類誤判心理學。
我們如果想理性思考、做出正確決策,首先得想想自己何時不理性、做出錯誤決策,這些錯誤決策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些原因是系統性的,把它們列成清單,這樣就能有意識地去避免。查理最終總結出一套人類誤判心理學,系統列出了人類在二三十種情況下會不斷犯同樣錯誤的情況。
企業家是需要有熱情、有企圖心的,但要是不斷陷入系統性錯誤,就很難成功。這就是為什么創業的人不少,想創業的人更多,但成功的沒那么多。有些看似瘋狂的事,其實很合理,有些看似合理的,反而是大錯特錯。
4.基于常識
他所講理性的第四個方面,是基于常識。
在查理看來,常識是最稀缺的認知,這種認知是通過實踐總結出來的,違背常識就會付出代價,而這些代價反過來能印證這些常識。
所以他有個關于理性很重要的觀點——重復那些已被實踐證明正確的做法,避免被實踐證明錯誤的做法。這一點極為重要。
查理非常推崇李光耀、鄧小平,他們都以超越意識形態的常識,帶來大的發展。
李光耀建國時,國內70%是華人,按說國家語言應該用華語,但他選擇英語為主、華語為輔,后來證明這是極其重要的決定。
鄧小平搞改革時,能夠果斷嘗試探索中國的市場經濟,用實踐檢驗真理,“摸著石頭過河”,讓中國走出一條全新道路。
查理所講的常識、理性,確實不像常人理解的那么簡單,不是僅靠邏輯就行的。很多人用邏輯討論問題,聽起來很理性,但那叫合理化,是用理性的語言來維護自己預設立場,聽起來有理,實際是自我辯護。
普世理論、多學科重要研究成果的交叉運用、避免系統性非理性心理狀態(人類誤判心理學)以及他所強調的常識,聽起來簡單,但古今中外違背常識的情況比比皆是,都會付出不小的代價。
馬斯克與芒格,
是不是“同類”?
孫允廣:像喬布斯、馬斯克,他們的一些想法完全非常OPEN,非常顛覆。馬斯克的“筷子夾火箭”完全顛覆了我們現有的認知,這種顛覆是否與芒格的常識有沖突?
李錄:一點都不會,馬斯克和查理在理性思維上極為相似。
查理的“普世智慧思維”,與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本質是同一回事,是一種科學思維方式,也就是物理學思維方式。
我們研究所有事物,都要從事實出發,推導出合乎邏輯的結論,而結論正確與否,實際取決于基本的事實、基本的假設以及推理的過程,這其實就是物理學、數學等所有現代科學的基礎思維。
但絕大部分人并不會把這種思維運用到科學之外的其他方面,而那些真正秉持純粹理性的人,會把這種思維方式推廣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它來檢驗我們做的諸多事情,包括做決策。
馬斯克第一次講火箭回收的設計概念是在TED會議上,當時我就坐在第一排。他斷言,如果成功了,會把上天發射的成本降低99%,將來用不到50萬美金,大家就能到月球上去轉一圈,當時在場很多觀眾都舉手表示愿意參加,這已經好多年前了。
后來,在一次午餐會上,查理、馬斯克、我,還有另外一個人,我們四個人一起討論了電池和各種各樣的科學問題,其實查理和馬斯克在思維高頻上完全同頻。不過在商業判斷上,大家對風險的看法不太一樣。
馬斯克認為哪怕只有5%的成功概率,也應該去做,因為回報率很高,這和風險投資(VC)的想法一樣,但可能要做一百家這樣的公司,押注中間總會有一些成功的。但對于查理來說,他可能需要80%以上的成功概率才會去做,這樣的話,他可能只需要投五家公司就行。
這就是不同的選擇,是用VC的方式投資,還是用查理的方式投資,其實就是個投資偏好問題。對于創業者而言,是在80%還是5%成功可能性去做,這也是風險承受問題。如果認為需要80%成功率才去做,可能競爭比較激烈,所以一般創業者,風險承受能力都比較高。
馬斯克、王傳福在做電動車之前,美國乃至全球差不多有將近100年都沒有大型汽車公司成功的案例了,最近的可能還是韓國汽車的崛起。
這時候,特斯拉和比亞迪決定重新挑戰,當然他們成功的幾率不高,而且采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王傳福采用的方式是,用他已成功的現有公司的現金流去扶持那些成功概率不高但成功后回報非常高的企業。
特斯拉采取的辦法是借助美國成熟的金融市場支持,通過風險投資,還有奧巴馬時代政府對電動車的特殊支持,才渡過了幾次可能失敗的危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的支持以及中國上海工廠的支持,也是它成功的重要原因,所以特斯拉幾次瀕臨失敗,最終成功,這體現的就是企業家精神。
如何在成功概率比較小的情況下,動用所有資源,讓成功的概率在自己的掌控下增加,這是不同于查理的另一種做法。
但基本思維方式大家都是一樣的,就是用概率的思維方式。馬斯克也會很清楚地告訴你,他說自己做這件事的時候,成功的概率極低,但這件事值得做,而且成功之后回報很高,這也是風險投資的基本邏輯。
如何看待AI?
孫允廣:最后,我們聊聊AI,這個繞不過去的前沿話題。
您曾有一個觀點,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實現指數級發展,是因為知識交換能達到“1+1>4”的效果。但如今在AI的助力下,知識好像平權化了,不管博士還是普通人,在AI面前似乎都被拉到了同一水平線上。
您是如何理解AI的?另外,在AI時代,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新的投資邏輯呢?
李錄:AI確實是當下最為重要的技術了,我主要有三個想法。
我第一個觀點是,AI技術是全方位、劃時代的技術,只是這劃時代的具體情況現在還很難說清楚。
首先,如果把AI跟過往的重要發明和發現相比的話,我們不清楚它到底在什么層級。
iPhone出現、互聯網誕生、蒸汽機發明、農業出現或者火的發現這些都是里程碑式事件,同時火比農業重要,農業發明、蒸汽機發明、輪子的發明等又各有其獨特且重大的影響,它們一步步走來,對全球的持續影響都不一樣。
當下,我們知道AI是一項全方位的技術,它會影響人類生活和商業的方方面面,可它具體怎么影響、影響到何種程度,現在沒人能說得清楚。
我的第二個觀點是,AI是給人類帶來巨大希望,同時也可能伴隨巨大生存危機的技術。
這里說的生存危機并非指AI一旦全方位超越人類,就會馬上消滅人類,它有可能把人類當作工具,就像我們對待地球上其他物種一樣,我們把它們當作食物、景觀、繁殖對象、能量來源等等,寵物算是其中最高級別的“工具”了,并非我們對其他物種有與生俱來的愛憎,而是因為我們的智能遠超它們,很難對它們產生同理心。
如果AI智能遠超人類各方面,那讓它對人類具備同理心就太難了。
我的第三個觀點是,AI技術必須朝著可控制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政府和私營部門全方位合作,針對AI發展及時構建可行的治理架構,而且這個架構要把全人類所有的政府和私營部門團結起來。
AI問題對全人類而言,就如同和外星人接觸、經歷過的病毒大瘟疫以及二十世紀面臨的核威脅一樣,屬于全人類共同的威脅、挑戰與機遇,既是巨大機遇,也是巨大挑戰,所以AI的出現需要全人類,需要政府和私營部門全方位合作,構建出合理有效的治理方式。這就是我對AI的三點大致看法。
孫允廣:這里面存在一個思維上的交鋒點,按照阿西莫夫機器人三原則理論,人工智能必須在人類的控制之下。但對于一個復雜系統,如果要控制它,控制系統需要比這個系統更復雜。由此就引出一個問題,人類能否造出比自己更復雜、更有智慧的東西呢?
李錄:人類本身是自然進化而來的,從大猩猩進化到人類,基因變化大概僅在2%到3%左右,且這種進化很多時候具有偶然性。
從科學思維角度來看,整個宇宙中,絕大部分事物是不相關的,一部分相關,還有一部分高度相關,我們將高度相關的部分稱作物理學定律,不過這些定律在特定條件下也會改變,宇宙實則是各種事物相互關聯的整體。
AI之所以靈活好用,關鍵在于它能為諸多因素建立相關性。
人類通過創造工具,過去十年里計算能力提升了一百萬倍,往后或許還會有數百萬倍的增速,隨著計算能力不斷提升,我們能夠利用所有數據以及人類產生的全部信息進行計算,進而建立起相關性科學,而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由此產生的智能雖然未必與人類智能相同,但可能包含人類智能,就像從大猩猩到人類的進化,雖然基因區別不大,但人類涵蓋了大猩猩的智能且實現了超越。
如今,如果建立起相關性科學,便能在數兆億的因素中構建相關性,并且是科學的相關性,比如我們當下的對話,其進行方式有著成千上萬種排列組合,但最終呈現的這一種,是相關性在起作用,你我都難以預測。
而AI憑借強大的計算能力,對我們及其他在線人員近期思考的問題做高度相關處理,能在幾億種可能性里判斷出當下環節出現的可能,這是此前不具備的能力。
另外,就像大猩猩與人類在很多問題的考量上,道德判斷和標準都不一樣,我們卻因為智能遠超它們,所以并不在意大猩猩的道德標準和它們關心的事情一樣,當人類不再是地球上最智能的物種,且該更智能的物種能自行高速進化、無需人類控制時,人類便面臨生存威脅了。
至于它會發展成何種物種,對我們而言既不重要也難以理解,就像大猩猩不理解我們為何討論這些問題一樣。
并且,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極為狹隘,世界95%都是暗物質和暗能量,我們一無所知,世界是否平行也不清楚,如果有更高智能的物種關心這些,對我們來說遙不可及,這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實實在在的風險。
盡管當下存在中美之間的競爭,以及中東、烏克蘭和俄羅斯等地的局勢問題,但人類更多面臨的是共同挑戰。
在此情形下,更需要查理所倡導的大家共同合作的精神。他一生極為推崇和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特別希望中美之間能長期合作,這可謂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中美兩國都有許多尊重并相信他理念的人,而且他始終堅信中美之間應永久性合作,我也由衷希望有朝一日這能成為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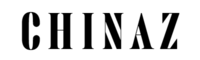











 蜀ICP備19031620號
蜀ICP備19031620號